心理学家Paul Ekman揭示了查尔斯·达尔文对同情心的真实看法——这可能与你想象中的达尔文视角不同。达尔文认为利他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观点正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 作者:Line Goguen-Hughes
- 2010年12月23日
- 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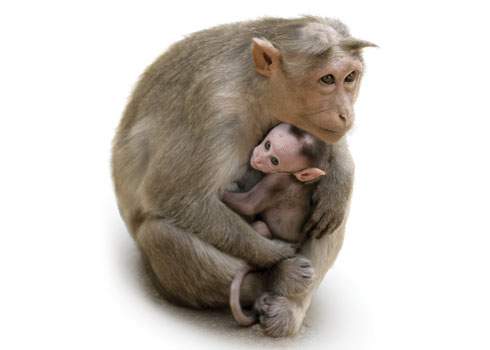
一只猕猴和它的宝宝。照片© Sergey Mateev / Dreamstime.com
1871年,在他去世前11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一本被称为“最伟大的未读之书”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书中关于同情心的讨论揭示了达尔文的一个鲜为人知的观点,这与通常被认为自私、竞争激烈的达尔文主义视角相悖。
在第四章,题为“人类与低等动物心智能力的比较”中,达尔文解释了他所说的“同情”(今天称为共情、利他或同情)的起源,描述了人类和其他动物如何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其他生物。虽然他承认这种行为最有可能发生在家庭群体内部,但他写道,最高的道德成就是关心所有生命的福祉,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
鉴于查尔斯·达尔文对物种连续性的承诺,他声称关心他人福利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这一点也不奇怪。达尔文讲述了一个故事:“几年前,伦敦动物园的一位饲养员向我展示了他脖子后部一些深而几乎愈合的伤口,这些伤口是在他跪在地上时被一只凶猛的狒狒咬伤的。那只小美洲猴子是这位饲养员的好朋友,住在同一个围栏里,非常害怕这只大狒狒。然而,当它看到自己的朋友处于危险之中时,它冲过去救援,通过尖叫和咬的方式分散了狒狒的注意力,使饲养员得以逃脱。”这个事件与F.B.M. de Waal在2004年的研究《论动物共情的可能性》一致。
达尔文说,这种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最大是在帮助者与需要帮助的人有亲属关系的情况下。“首先很明显的是,”他在《人类的由来》中写道,“对于人类来说,本能冲动有不同的强度;野蛮人会冒生命危险去拯救同社区的成员,但对陌生人则完全漠不关心;一位年轻且胆小的母亲受到母爱本能的驱使,会在没有任何犹豫的情况下冒着最大的危险去救她的婴儿……”
然而,达尔文认识到,有些人会对完全陌生的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帮助,而不仅仅是亲人或爱人。“尽管如此,许多从未冒险救过人的文明人,在勇气和同情心的驱使下,不顾自我保护的本能,毫不犹豫地跳入激流中救起溺水的人,尽管是个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人被同样的本能动机所驱使,就像那只勇敢的小美洲猴子为了救它的饲养员而攻击那只巨大而可怕的狒狒一样。”达尔文的这一思路已被K.R. Munroe在1996年的研究《无私的心:对共同人性的感知》所证实。
达尔文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有某些人会对陌生人表现出同情心,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这种关心是由基因决定的,还是仅由成长环境决定的,或者是两者混合的结果?达尔文也没有写到是否可以通过培养来增强那些没有这种同情心的人。
今天,这些问题成为理论(见P. Gilbert编著,《正念》,Routledge, 2005)和实证研究(D. Mobbs等人,《相似性在替代奖励中的关键作用》,Science, 2009)的主题。在《心理公报》上的文章《共情:进化分析和实证评论》中,Goetz, Keltner和Simon-Thomas分析了有关共情、利他和同情的心理学文献,结合新的证据,他们认为应该将同情视为一种情绪。在即将发表的文章《共情与利他:一个重新表述和研究议程》中,Erika Rosenberg和我认为家族共情是一种情绪,尽管目标有限,但我们认为将其他形式的共情归类为情绪并不合适。
达尔文提供了对同情心起源的解释:“我们之所以被驱使去减轻他人的痛苦,是为了同时减轻我们自己的痛苦感受……”然而,正如佛教学者B. Alan Wallace指出的,不是所有人都以这种方式回应痛苦。他指出,一个人可能会想,“我很幸运我不是那个人。”许多年前在我的研究中发现,大约三分之一观看痛苦视频的人在自己脸上也表现出痛苦,但同样数量的人对痛苦的景象表现出厌恶。这些比例在日本东京和美国加州的人群中相同,表明反应不受文化影响。
达尔文还描述了自然选择如何有利于同情心的进化,无论最初的行为动机是什么:“无论这种感觉多么复杂,由于它对所有互相帮助和保卫对方的动物的重要性,它会通过自然选择而增加;因为那些包括最多同情成员的社区将会发展得最好,并养育最多的后代。”
然而,与达尔文的预期相反,今天没有任何国家,或已知的历史上,大多数人口对陌生人表现出同情和利他行为,达尔文后来在同一章节中更现实地描述了同情的范围。
达尔文在讨论同情心和利他的起源和性质时,描述了他认为最高尚的道德美德。他写道:“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小部落联合成更大的社区,简单的推理会告诉每个个体,他应该将社交本能和社会同情扩展到所有民族的成员,即使他们对他来说是陌生人。一旦达到这一点,就只有一个人为的障碍阻止他的同情延伸到所有民族和种族的人。如果他们看起来不同,经验不幸地告诉我们,要多久才能把他们看作我们的同类。超越人类界限的同情,即对低等动物的仁慈,似乎是最后获得的道德品质之一……这种美德,即对较低动物的关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高贵的品质之一,似乎偶然地从我们越来越温柔和广泛传播的同情中产生,直到它扩展到所有有感知的生物。”
在我与达赖喇嘛关于情绪和同情的讨论中,基于我们合作的书籍《情绪意识》,我向他读了这段达尔文的最后一段引用。达赖喇嘛的翻译Thupten Jinpa惊叹道,“他用了‘所有有感知的生物’这句话吗?”Jinpa感到惊讶,因为这句话正是佛教对菩萨无边慈悲的英文翻译。
查尔斯·达尔文在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中很少有人持有这种观点,只有在20世纪下半叶,对非人类生物的同情才变得更加流行。达尔文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
达尔文至少在写《人类的由来》时对佛教有所了解。J.D. Hooker是达尔文最亲密的朋友,在喜马拉雅山脉度过了多年。达尔文的主要学者Janet Browne告诉我,“达尔文很可能在Hooker从锡金和其他印度地区旅行后与他讨论过这类问题”,Alison Pearne,也是《进化:查尔斯·达尔文的精选信件》的编辑之一,指出Hooker在从印度寄给达尔文的信中提到了佛教。尽管如此,达尔文关于道德和同情的核心思想出现在1838年的笔记本中,比他遇到Hooker早两年。
达尔文的曾孙Randal Keynes描述了达尔文在这些笔记本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如下:“他的评论措辞随意,但他对基本目标毫无疑问。[达尔文写道]‘我们的对错感是否源于反思我们不断发展的智力能力以及与本能的爱和对他人的关心联系起来的行为?如果我们有任何具有社会本能的动物发展出反思的能力,它必须有一个良知。’
达尔文在他的M笔记本中写道:“不考虑起源……个人忘记了自己,并帮助、保护和为他人行动,不惜牺牲自己。”达尔文也对道德的起源感兴趣:“判断幸福的原则时,我们必须向前看,关注一般行为——当然,因为它是我们远古以来幸福的结果……没有道德感,社会无法存在。”
达尔文承认他对大卫·休谟的债务。1838年,达尔文阅读了休谟的《道德原则探讨》,认为这对发展一个脱离神学指导的理论很重要。正如Randal Keynes在《达尔文、他的女儿与人类进化》中所说:
大卫·休谟将共情置于其关于自然道德原则来源的思考中心。他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感觉,而不是基于某种抽象概念的理性态度。“我们心中有些善意,不管多么微小,都被注入了一些对人类的友好;我们框架中的一些鸽子元素,与狼和蛇的元素交织在一起。”查尔斯现在发展了这一想法,并推测我们的道德感也可能自然地从这种感觉中生长出来。[达尔文写道]“从自然学家的角度看待人类,就像看待任何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可以得出结论,他具有亲子、婚姻和社会本能……这些本能由对对象的爱或善意组成……这种积极的共情使个人忘记自己,帮助、保护并为他人行动,不惜牺牲自己。”
在《人类的由来》导言的结尾,James Moore和Adrian Desmond写道,一些同时代的研究者强调了达尔文维多利亚价值观的“人道方面:责任、无私和同情……弗朗西斯·科贝[一位女权主义者和早期动物权利活动家]原谅那些能想象‘作者是一个有着异常慷慨和宽容天性的人,并将这种天性归因于整个物种,然后据此进行理论化’的读者。”
达尔文对同情心、利他主义和道德的思考确实揭示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关注点,与那些只关注“适者生存”(事实上这是斯宾塞的名言,而非达尔文)的人所描绘的画像截然不同。那些不熟悉他著作的人,甚至是某些科学家,都不知道达尔文对人类统一性的承诺、废奴信念以及对道德原则和人类及动物福利的浓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