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脑让我做的
随着科学家们对大脑结构如何影响我们行为的了解越来越多,Sharon Begley 问: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是可以简单地归咎于我们的大脑?
- 作者:Sharon Begley
- 2013年10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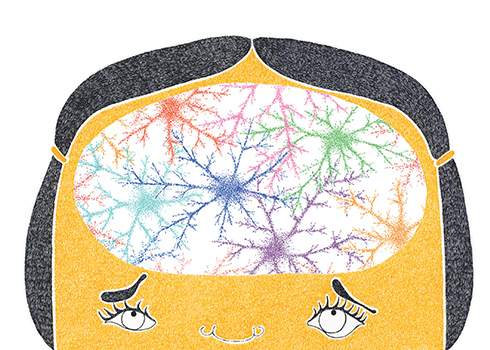
插图由 Malin Rosenqvist 绘制
我们更尊重什么,大脑还是心灵?
这似乎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根据所有专家的说法,心灵只是大脑的行为。心灵是通过人类大脑中大约100万亿个突触的电和化学活动产生的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输出。所以问题就像在问你更重视什么:空调吹出的凉爽空气还是空调本身。(我正在一个96度的日子里写这篇文章;如果你是在冬天读这篇文章,请用“暖气”和“加热器”代替)。
大脑一直在用生物学解释来取代心灵对人类行为的解释。随着神经科学在理解心理现象方面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心灵都越来越落后。因此,当大脑生物学成为解释“心理”现象的充分方式时,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以前属于哲学而非科学领域的两难困境。
例如,几年前,弗吉尼亚州的一名中年男子开始收集儿童色情内容,并最终猥亵了他8岁的继女。被捕并关押等待审判时,他开始抱怨头痛和眩晕。脑部扫描显示,他的额叶区域有一个大肿瘤侵入了调节性行为的下丘脑结构。这名男子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所以从法律上来说,他有“完整的认知能力和道德知识”。但由于肿瘤的存在,医生说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异常行为。
肿瘤被切除后,他被判无罪,他的性兴趣也恢复了正常。但几个月后,他又开始痴迷于未成年女孩。再次扫描发现,第一次手术中未完全切除的组织碎片又长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肿瘤。手术再次使他恢复正常。
现在想象一下,一名29岁的失业大学生与父母同住,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发短信给朋友、玩电子游戏、查看Facebook。当心烦意乱的父亲问他什么时候打算找工作时,他说医生刚刚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他有一个脑动脉瘤,导致他感到倦怠、抑郁,无法计划、思考清晰或采取行动。但如果外科医生能修复动脉瘤,儿子说,他相信他会扭转局面。
但如果儿子只是回答:我不想这样做。这会让你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吗?
当涉及到劫持我们的自由意志时,大多数人会更宽容那个有动脉瘤的年轻人,而不是那个只是不想找工作的人。那是因为当我们寻找行为的原因时,基于大脑的解释——它们是物理的、具体的、可见的(如果打开懒惰儿子或恋童癖继父的头骨)——比模糊的心理学解释更有说服力。在许多研究中,受访者表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比对自己的神经状态负更多责任。大多数人在看到某人的选择似乎是由于一个实体如肿瘤或动脉瘤所决定时,会原谅他们。然而,他们不愿意原谅那些因心理状态(如缺乏动力或执行功能差)而做出的行为。
但每一种行为的原因都在大脑中,即使这种原因(异常的活动模式、布线故障)不像肿瘤那样明显。毕竟,大脑是“行为器官”,就像胰腺是“胰岛素生产器官”。
如果我们对心理学的看法不同于神经学,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出现了:当越来越多曾经被认为是心理学的现象被用电流回路和化学成分解释——简而言之,作为神经生物学——时,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的同胞以及我们自己所做的事?
一些线索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实验,哲学家们向数百名志愿者展示了类似懒惰儿子类型的情景。
在一个版本中,一名中年男子被描述为经常有关于未成年的男孩的性幻想,并经常透过窗户窥视13岁的邻居洗澡。研究人员告诉志愿者,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患有休伯纳妄想症,这是一种以“过度心理活动”为特征的心理疾病,或者因为他患有赫马托体病,这是一种神经疾病,其中树突状肝细胞接管了大脑。
在另一个情景中,一名妇女闯了红灯,要么因为她太分心和沮丧于即将到来的离婚而无法专注于道路,要么因为她的悲伤导致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下降,切断了视觉皮层的氧气供应,导致其处理视觉信息的速度变慢且不准确。
在每种情况下,这些条件都是编造的(既没有休伯纳妄想症也没有赫马托体病),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心理学(心灵)的解释,另一个是神经学(大脑)的解释。
结果发现,神经学解释比心理学解释更容易让志愿者说施害者不应承担责任。例外的是,人们真的非常抵制用大脑化学物质来为暴力或恋童癖等令人厌恶的行为辩解。学者们怀疑,这是因为我们虽然都看过权威的大脑图谱,将前额叶皮层标记为执行功能的部位,将边缘系统标记为情绪的中心,但我们仍然紧紧抓住一个观念:里面还有些东西不在图谱上:一个“我”。
这个“我”就是英国哲学家Gilbert Ryle轻蔑称之为“机器中的幽灵”的实体,它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大脑的物理性存在,并且作为一个非物质的存在,比大脑所能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强大。这个“我”是最终的决策者,观察者,可以在前扣带皮质过度活跃引起强迫症时说,安静点! 或者在内侧前额叶皮质(冲动控制的部位)活动不足之前做些什么鲁莽的事时喊道,振作起来! 亚利桑那大学的哲学家Shaun Nichols认为,只要我们相信有一个独立于大脑的“我”,我们就会“拒绝认为决策是由确定性的机制和过程产生的。”对于2007年一本书提出的标题问题,《我的神经元让我做了吗?》,我们说不。
这绝不是外行人的天真信念。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神经科学家Michael Gazzaniga断言,“我们是负责任的代理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正如他在2011年的书《谁在掌控?自由意志与大脑的科学》中所说。我们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信念,即我们人类有一个“自我”在做出所有关于我们的行为的决定,这种信念的推论是,这个自我可以在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情时介入并说,停下来!
当然,有无数的心理现象是神经科学家无法解释的,比如为什么感觉会这样,想象力是从哪里来的,解释是一回事,预测则是另一回事(就像天气预报)。但是毫无疑问,科学家们正在逐步解开我们思考、感受和行动的机制,每一次发现都为“我”留下了更少的空间。考虑到当哥白尼将地球从太阳系中心移开时,人类感到多么渺小甚至惊恐,我们可以想象,当只剩下“我的大脑”而没有“我”时,我们会有什么感觉。
Sharon Begley 是 Reuters 的高级健康和科学通讯员,《Train Your Mind, Change Your Brain》的作者,也是《The Emotional Life of Your Brain》的合著者之一。
这篇文章也出现在2013年12月的《正念》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