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最佳共情训练练习与活动
28 十一月 2024
12 Best Compassion Training Exercises & Activities
1 May 2019 by Elaine Houston, B.Sc.
Scientifically reviewed by Jo Nash, Ph.D.
 在本文中,您将了解通过训练培养共情的过程以及如何衡量共情。
在本文中,您将了解通过训练培养共情的过程以及如何衡量共情。
我们将讨论一些方法来将更多的共情引入您自己的生活,以及您的客户的生活。
祝全世界充满更多共情!
在继续之前,您可以免费下载我们的三个自我共情练习工具。这些详细的、基于科学的练习将帮助您增加对自己和客户的共情与善意。
本文包含
- 什么是共情训练?
- 共情可以被教授和训练吗?
- 我们如何最好地培养共情?
- 区分共情与其他构造
- 共情的三种取向
- 共情可以被测量吗?
- 共情量表
- 对他人共情量表
- 5个测试、测验和问卷
- 12个练习与活动用于训练共情
- 在教育中教授共情
- 什么是共情培养训练?
- 什么是共情项目?
- 其他培训计划和选项(包括在线)
- 收尾信息
- 参考文献
什么是共情训练?
共情是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日益增长的兴趣点。共情的研究从进化科学、心理科学和神经科学的不同角度进行,并且经常与精神导师合作,以增强我们对共情及其相关益处的理解(Kirby, 2017)。
心理学中对共情的定义各不相同,有些研究者认为它是情感(Batson, 1991),生物特征(Gilbert, 2014),或是一个多维结构(Jazaieri et al., 2014)。
尽管定义不同,但大家普遍认为共情由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组成。Jazaieri等人(2014)将共情定义为一个复杂的多维结构,包含四个组成部分:
- 认知成分(对痛苦的认知)
- 情感成分(同情,即因受苦而产生的情感波动)
- 意图成分(希望减轻痛苦)
- 动机成分(回应或准备帮助减轻痛苦)
由于定义不同,开发出多种方法和干预措施作为提升自身及他人的共情技能的途径。
个体和社会福祉的一个关键方面,共情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Jazaieri et al., 2014)。共情训练可以在任何年龄开始,并涉及训练大脑以发展特定的技能,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对待他人,同时努力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更具有共情性。
虽然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共情,但对于一些人来说,通过训练和实践进一步提升这些技能可能是有益的。
幸运的是,培养共情并不需要多年的承诺,实际上可以很快进步。Mantelou和Karakasidou(2017)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短短七分钟的干预也能增加亲近感和联系感,改善共情和生活满意度,这比没有接受共情训练的人要好。
共情训练的重点不仅在于痛苦,还在于支持和鼓励对自我和他人的共情。
通过一系列的呼吸、姿势、想象技巧和回忆技巧,使参与者能够体验共情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
本质上,共情训练有助于在脑海中形成可以实现的想法(Gilbert, 2014)。
研究表明,共情对心理健康、情绪调节以及人际和社会关系都有积极影响(Kirby, 2017),因此培养共情显然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Fredrickson等人(2008)考察了共情冥想对情绪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共情冥想的参与者经历了积极情绪的增加、抑郁症状的减少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Allen和Knight(2005)提出共情对于缓解抑郁和其他负面情绪状态的重要性。
根据他们的研究,共情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人上可以减轻抑郁中的消极自我关注,转变为共情中的积极他我关注。此外,共情似乎可以缓解社交孤立的负面症状。
鉴于这些显著的好处,心理疗法和共情导向的干预措施现在已经被开发出来,专门旨在培养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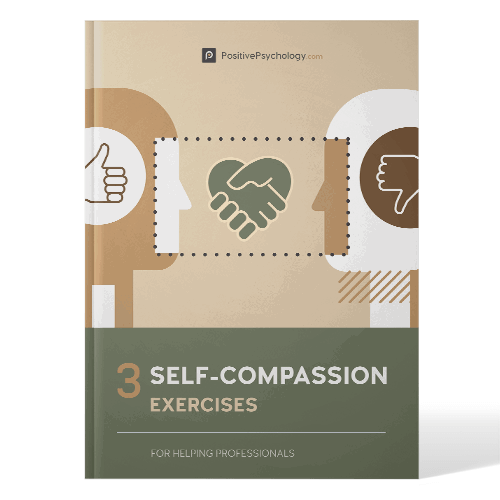
下载3个免费的自我共情工具包(PDF)
通过填写以下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
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必需)
您的专长(必需)
您的专长TherapyCoachingEducationCounselingBusinessHealthcareOther
电子邮件
此字段用于验证目的,不应更改。
window.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 function() { /* <![CDATA[ */ gform.initializeOnLoaded( function() {gformInitSpinner( 3, 'https://positivepsychology.com/wp-content/plugins/gravityforms/images/spinner.svg', true );jQuery('#gform_ajax_frame_3').on('load',function(){var contents = jQuery(this).contents().find('*').html();var is_postback = contents.indexOf('GF_AJAX_POSTBACK') >= 0;if(!is_postback){return;}var form_content = jQuery(this).contents().find('#gform_wrapper_3');var is_confirmation = jQuery(this).contents().find('#gform_confirmation_wrapper_3').length > 0;var is_redirect = contents.indexOf('gformRedirect(){') >= 0;var is_form = form_content.length > 0 && ! is_redirect && ! is_confirmation;var mt = parseInt(jQuery('html').css('margin-top'), 10) + parseInt(jQuery('body').css('margin-top'), 10) + 100;if(is_form){jQuery('#gform_wrapper_3').html(form_content.html());if(form_content.hasClass('gform_validation_error')){jQuery('#gform_wrapper_3').addClass('gform_validation_error');} else {jQuery('#gform_wrapper_3').removeClass('gform_validation_error');}setTimeout( function() { /* delay the scroll by 50 milliseconds to fix a bug in chrome */ jQuery(document).scrollTop(jQuery('#gform_wrapper_3').offset().top - mt); }, 50 );if(window['gformInitDatepicker']) {gformInitDatepicker();}if(window['gformInitPriceFields']) {gformInitPriceFields();}var current_page = jQuery('#gform_source_page_number_3').val();gformInitSpinner( 3, 'https://positivepsychology.com/wp-content/plugins/gravityforms/images/spinner.svg', true );jQuery(document).trigger('gform_page_loaded', [3, current_page]);window['gf_submitting_3'] = false;}else if(!is_redirect){var confirmation_content = jQuery(this).contents().find('.GF_AJAX_POSTBACK').html();if(!confirmation_content){confirmation_content = contents;}jQuery('#gform_wrapper_3').replaceWith(confirmation_content);jQuery(document).scrollTop(jQuery('#gf_3').offset().top - mt);jQuery(document).trigger('gform_confirmation_loaded', [3]);window['gf_submitting_3'] = false;wp.a11y.speak(jQuery('#gform_confirmation_message_3').text());}else{jQuery('#gform_3').append(contents);if(window['gformRedirect']) {gformRedirect();}}jQuery(document).trigger("gform_pre_post_render", [{ formId: "3", currentPage: "current_page", abort: function() { this.preventDefault(); } }]); if (event && event.defaultPrevented) { return; } const gformWrapper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gform_wrapper_3" ); if ( gformWrapperDiv ) { const visibilitySpan = document.createElement( "span" ); visibilitySpan.id = "gform_visibility_test_3"; gformWrapperDiv.insertAdjacentElement( "afterend", visibilitySpan ); } const visibilityTest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gform_visibility_test_3" ); let postRenderFired = false; function triggerPostRender() { if ( postRenderFired ) { return; } postRenderFired = true; jQuery( document ).trigger( 'gform_post_render', [3, current_page] ); gform.utils.trigger( { event: 'gform/postRender', native: false, data: { formId: 3, currentPage: current_page } } ); if ( visibilityTestDiv ) { visibilityTestDiv.parentNode.removeChild( visibilityTestDiv ); } } function debounce( func, wait, immediate ) { var timeout; return function() { var context = this, args = arguments; var later = function() { timeout = null; if ( !immediate ) func.apply( context, args ); }; var callNow = immediate && !timeout; clearTimeout( timeout ); timeout = setTimeout( later, wait ); if ( callNow ) func.apply( context, args ); }; } const debouncedTriggerPostRender = debounce( function() { triggerPostRender(); }, 200 ); if ( visibilityTestDiv && visibilityTestDiv.offsetParent === null ) { const observer = new MutationObserver( ( mutations ) => { mutations.forEach( ( mutation ) => { if ( mutation.type === 'attributes' && visibilityTestDiv.offsetParent !== null ) { debouncedTriggerPostRender(); observer.disconnect(); } }); }); observer.observe( document.body, { attributes: true, childList: false, subtree: true, attributeFilter: [ 'style', 'class' ], }); } else { triggerPostRender(); } } );} ); /* ]]> */ );
共情可以被教授和训练吗?
共情是一种强大的人类体验,而且可以通过训练来培养。Weng等人(2013)建议,通过训练可以培养共情,并且更大的利他行为可能源自于对他人苦难的更深入理解。
共情干预的研究表明,心理幸福感和社交联系都有显著改善(Neff & Germer, 2017),共情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共情训练不仅关注痛苦,还支持和鼓励对自我和他人的共情。
通过一系列的呼吸、姿势、想象技巧和回忆技巧,参与者有机会体验到共情是什么,或者可以成为什么。
本质上,共情训练有助于在脑海中形成可以实现的想法(Gilbert, 2014)。
研究表明,共情对心理健康、情绪调节以及人际和社会关系都有积极影响(Kirby, 2017),因此培养共情显然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Fredrickson等人(2008)考察了共情冥想对情绪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共情冥想的参与者经历了积极情绪的增加、抑郁症状的减少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Allen和Knight(2005)提出共情对于缓解抑郁和其他负面情绪状态的重要性。
根据他们的研究,共情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人上可以减轻抑郁中的消极自我关注,转变为共情中的积极他我关注。此外,共情似乎可以缓解社交孤立的负面症状。
鉴于这些显著的好处,心理疗法和共情导向的干预措施现在已经被开发出来,专门旨在培养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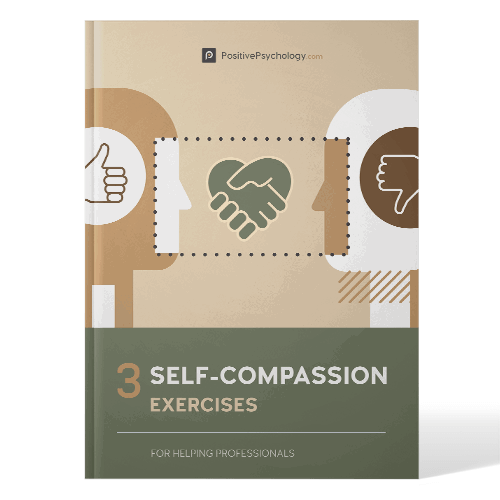
下载3个免费的自我共情工具包(PDF)
通过填写以下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
姓名
电子邮件地址(必需)
您的专长(必需)
您的专长TherapyCoachingEducationCounselingBusinessHealthcareOther
电子邮件
此字段用于验证目的,不应更改。
window.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 function() { /* <![CDATA[ */ gform.initializeOnLoaded( function() {gformInitSpinner( 3, 'https://positivepsychology.com/wp-content/plugins/gravityforms/images/spinner.svg', true );jQuery('#gform_ajax_frame_3').on('load',function(){var contents = jQuery(this).contents().find('*').html();var is_postback = contents.indexOf('GF_AJAX_POSTBACK') >= 0;if(!is_postback){return;}var form_content = jQuery(this).contents().find('#gform_wrapper_3');var is_confirmation = jQuery(this).contents().find('#gform_confirmation_wrapper_3').length > 0;var is_redirect = contents.indexOf('gformRedirect(){') >= 0;var is_form = form_content.length > 0 && ! is_redirect && ! is_confirmation;var mt = parseInt(jQuery('html').css('margin-top'), 10) + parseInt(jQuery('body').css('margin-top'), 10) + 100;if(is_form){jQuery('#gform_wrapper_3').html(form_content.html());if(form_content.hasClass('gform_validation_error')){jQuery('#gform_wrapper_3').addClass('gform_validation_error');} else {jQuery('#gform_wrapper_3').removeClass('gform_validation__error');}setTimeout( function() { /* delay the scroll by 50 milliseconds to fix a bug in chrome */ jQuery(document).scrollTop(jQuery('#gform_wrapper_3').offset().top - mt); }, 50 );if(window['gformInitDatepicker']) {gformInitDatepicker();}if(window['gformInitPriceFields']) {gformInitPriceFields();}var current_page = jQuery('#gform_source_page_number_3').val();gformInitSpinner( 3, 'https://positivepsychology.com/wp-content/plugins/gravityforms/images/spinner.svg', true );jQuery(document).trigger('gform_page_loaded', [3, current_page]);window['gf_submitting_3'] = false;}else if(!is_redirect){var confirmation_content = jQuery(this).contents().find('.GF_AJAX_POSTBACK').html();if(!confirmation_content){confirmation_content = contents;}jQuery('#gform_wrapper_3').replaceWith(confirmation_content);jQuery(document).scrollTop(jQuery('#gf_3').offset().top - mt);jQuery(document).trigger('gform_confirmation_loaded', [3]);window['gf_submitting_3'] = false;wp.a11y.speak(jQuery('#gform_confirmation_message_3').text());}else{jQuery('#gform_3').append(contents);if(window['gformRedirect']) {gformRedirect();}}jQuery(document).trigger("gform_pre_post_render", [{ formId: "3", currentPage: "current_page", abort: function() { this.preventDefault(); } }]); if (event && event.defaultPrevented) { return; } const gformWrapper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gform_wrapper_3" ); if ( gformWrapperDiv ) { const visibilitySpan = document.createElement( "span" ); visibilitySpan.id = "gform_visibility_test_3"; gformWrapperDiv.insertAdjacentElement( "afterend", visibilitySpan ); } const visibilityTestDiv = document.getElementById( "gform_visibility_test_3" ); let postRenderFired = false; function triggerPostRender() { if ( postRenderFired ) { return; } postRenderFired = true; jQuery( document ).trigger( 'gform_post_render', [3, current_page] ); gform.utils.trigger( { event: 'gform/postRender', native: false, data: { formId: 3, currentPage: current_page } } ); if ( visibilityTestDiv ) { visibilityTestDiv.parentNode.removeChild( visibilityTestDiv ); } } function debounce( func, wait, immediate ) { var timeout; return function() { var context = this, args = arguments; var later = function() { timeout = null; if ( !immediate ) func.apply( context, args ); }; var callNow = immediate && !timeout; clearTimeout( timeout ); timeout = setTimeout( later, wait ); if ( callNow ) func.apply( context, args ); }; } const debouncedTriggerPostRender = debounce( function() { triggerPostRender(); }, 200 ); if ( visibilityTestDiv && visibilityTestDiv.offsetParent === null ) { const observer = new MutationObserver( ( mutations ) => { mutations.forEach( ( mutation ) => { if ( mutation.type === 'attributes' && visibilityTestDiv.offsetParent !== null ) { debouncedTriggerPostRender(); observer.disconnect(); } }); }); observer.observe( document.body, { attributes: true, childList: false, subtree: true, attributeFilter: [ 'style', 'class' ], }); } else { triggerPostRender(); } } );} ); /* ]]> */ );
我们如何最好地培养共情?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多数人类在核心层面都具有共情的能力。Warneken和Tomasello(2009)指出,共情是一种确保人类生存的自然且自动的反应。
他们的研究显示,年龄太小以至于还未学会礼貌规则的婴儿会自发地表现出帮助行为,即使没有奖励的承诺,甚至会克服障碍去帮助他人。
尽管如此,日常压力、社会压力和生活经历通常会使我们难以体验并充分表达对他人和自己的共情。然而,我们也有能力培育和发展一种更加共情的视角。
共情是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福祉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培育共情可以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实践。培养共情不仅仅是体验对他人的同情或关心,而是发展应对痛苦的能力、采取共情行动的能力,以及防止共情疲劳——这是一种极端的紧张和对他人的痛苦过度关注的状态(Allen & Leary, 2010)。这些品质支持各种目标,从小改善个人关系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
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兴趣领域,旨在了解如何通过共情训练方案培养和调节共情。根据Kirby(2017)的说法,目前至少有六种经过实证支持的干预措施专注于培养共情:
共情定向疗法
由Gilbert(2009)开发的共情定向疗法关注共情的两个心理学方面。第一是参与痛苦的动机,第二是行动的焦点,特别是为了帮助减轻和预防痛苦。
这种疗法专门为那些有严重和长期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设计,是一种综合和多模式的方法,旨在缓解内疚感和高水平的自我批评。通过共情定向疗法,那些难以激发某些积极情绪的人可以学会通过共情和自我共情练习来做到这一点。
自我共情疗法
自我共情疗法(MSC)由Neff和Germer(2013)开发,旨在帮助培养自我共情——即用对待好朋友一样的关怀、关心和支待自己。MSC结合了正念和自我共情的技能,以增强我们的情感健康能力。
这个程序面向普通公众,借鉴了藏传佛教的传统——融合传统的冥想和非正式的自我共情练习,结合了关于自我共情好处的循证文献。
MSC提供了自我共情和正念练习,以培养你的共情声音,并强调区分内在批评者和共情自我。
共情培养训练
共情培养训练(CCT)结合了传统冥想实践与当代心理学和科学研究,帮助你过上更有共情的生活。由Jinpa(2010)开发,CCT的理论基础来自藏传佛教和西方心理学。
CCT分为六个步骤进行共情练习训练(Kirby, 2017):
- 安定心灵,培养正念技能。
- 体验对自己所爱之人的慈爱和共情。
- 练习慈爱冥想(LKM)和对自己共情。
- 通过接纳我们的共同人性,对他人共情。
- 对所有生命共情。
- 实践共情行动,在想象中移除他人的痛苦,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给予他们。
基于认知的共情训练
基于藏传佛教中的“洛宗”理念,认知基础的共情训练(CBCT)训练实践者通过简单的冥想练习来培养共情。CBCT结合了正念和认知重构策略,通过反思自己和与他人的关系,鼓励转变视角(Reddy et al., 2012)。
情绪平衡培养
培养情绪平衡(CEB)计划基于西方关于情绪的科学研究和传统东方冥想实践,旨在建立情绪平衡(Ekman & Ekman, 2013)。
这种方法与其它共情导向的干预措施显著不同,因为它强调理解和识别他人的情绪。该培训方法通过教导和传授个体认识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并更有效地忍受痛苦的新方法,从而创建通向共情的路径。
共情和慈爱冥想
共情冥想(CM)或慈爱冥想(LKM)通常结合在一起,在共情导向的干预措施中共同练习,以帮助安定心灵,增加对自己的共情,改善心理健康。CM和LKM的目标是在心中表达善意、善良和温暖,方法是默念一系列咒语。
这两种做法都采用了一种结构化的办法,让人们可以学习将关爱的感觉首先指向自己,然后指向所爱的人,接着指向熟人,然后指向陌生人,接着指向与自己存在人际困难的人,最后无差别地指向所有生物(Galante, Galante, Bekkers, & Gallacher, 2014)。
如何培养共情 | 克强仁波切 - 学习佛教

区分共情与其他构造
共情常常被误解并且容易与相关的但不同的构造混淆(Shaver, Schwartz, Kirson, & O'Connor, 1987)。定义共情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定义它不是什么。这里将突出共情与其他概念的区别,如同理心、同情、怜悯和利他主义,以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
同理心
共情常被误认为是同理心,并且最有可能是因为每个概念都被认为与帮助有关。不同于共情,同理心不包括为了减轻他人的痛苦而采取行动的意愿,而是能够理解和与另一个人的感受融为一体。
De Waal(2008)描述了同理心是指能够感受并分享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并与对方感同身受,与对方站在同一立场。
同情
类似地,同情是指对某人的关心,并且通常伴随着希望看到他们更快乐的愿望。同情是对别人的不幸感到悲伤,但不一定与对方的视角或情感一致。
而共情则包含对他人情绪状态的认识,并且有采取行动的意愿去帮助他们。
怜悯
怜悯常被误认为是共情,但这两个概念非常不同——对他人困境的同情实际上是对其弱势地位的一种认可。
怜悯本质上是根植于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于他人(Fiske, Cuddy, Glick, & Xu, 2002)。而共情则不会认为对象是弱小或低下的,而是鼓励通过共同经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Ibbett, 2008)。
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出于对他人的福祉而行动,而共情包含了对痛苦的开放,以及在没有评判的情况下做出真正关切的行为(Jinpa, 2010)。值得注意的是,共情可以在缺乏利他行为的情况下存在。
爱
根据Jazaieri(2018)的说法,共情在功能上与最常见的两种爱的形式——浪漫爱情和父母对孩子的爱——不同。
这两种爱的主要区别在于,共情可能涉及复杂组合的多种积极和消极情绪。而爱通常与积极的情感和体验相关联,共情则是对痛苦的开放。
三种取向的共情

心理学对共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种特定的共情取向上,分别是:对他人的共情、从他人那里接收共情和支持自我共情。
在这里我们将探讨这些取向之间的差异。
接收共情
Jazaieri等人(2014)提出,感觉不到从他人那里接受善意可能会造成对接受共情的恐惧。对于某些人来说,成为他人的关怀对象可能会导致回避行为,以及负面情绪如悲伤或孤独(Gilbert, McEwan, Matos, & Rivis, 2011)。
改进这种共情取向可能增强人际关系和社会联系。它可以教会人们更舒适地成为他人的关注对象(Jazaieri等,2014)。
自我共情
由Neff(2007)定义,自我共情是指对自己的痛苦保持开放并有所触动。自我共情与许多积极特质相关。Neff(2007)认为自我共情对应对技巧、生活满意度、情绪智力、社会联系、目标掌握、主动性、好奇心、智慧、幸福、乐观和积极情绪都有正面影响。
自我共情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没有自我批评,这是焦虑和抑郁的早期预测因素之一(Blatt, 1995)。
自我共情的人倾向于认识到不完美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面对负面经历时,更有可能对自己友善。
针对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研究表明,高自我批判与对他人的共情、自我善意和幸福感呈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如果我们对自己过于苛刻,我们会对自己和他人都变得不那么共情(Beaumont, Durkin, Martin, & Carson, 2016)。
对他人的共情
对他人的共情在大多数文化和精神传统中都是明显的,并且有人认为对自己共情可能比对他人共情更容易接受(Jazaieri等,2014)。
然而,Gilbert及其同事(2011)认为,对他人的共情并不总是表达出来,有时甚至会被抑制或抑制。
起初,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理论结构和基本定义,人们认为自我共情和对他人的共情可能彼此相关。然而,由于它们大多被单独研究,关于它们的关系知之甚少。研究表明,两者可能不同,因为:
- 共情是针对他人而不是自己。
-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对自己比对他人更共情(Neff, 2003)。
共情可以被测量吗?
共情可以作为一个更大结构的子量表进行测量;然而,多年来,通过从其他量表中挑选项目,随后将其视为共情的测量标准。
为了探索共情、自我共情与其他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发了几种自我报告工具和量表来测量共情。目前有八个量表可以用来测量共情,每个量表的效度不同,并关注共情的不同方面(Strauss et al., 2016)。
共情爱量表(Sprecher & Fehr, 2005)——CLS包含21个自评项目,按1(完全不真实)到7(非常真实)的李克特量表评分。CLS适用于普通人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针对亲密的家庭成员和朋友,另一部分针对陌生人和全人类。
圣克拉拉简短共情量表(Hwang, Plante, & Lackey, 2008)——SCBC是共情爱量表的简短版本,由原始量表中的五个项目组成。与CLS不同,这个量表检查的是对陌生人的共情,而不是我们最亲近的人。
共情量表(Martins, Nicholas, Shaheen, Jones, & Norris, 2013)——该量表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可以在指导性培训中加强的共情测量。
自我共情量表(Neff, 2003)——SCS是一个包含26个项目的量表,采用5点响应量表从“几乎从不”到“几乎总是”。该量表不包括特别与注意感受相关的项目。
自我共情量表:简短版(Raes, Pommier, Neff, & Van Gucht, 2011)——这是一个包含12项的SCS简短版本,由原始六个子量表中的两项组成。简短形式的SCS在考察整体自我共情得分时与长量表有近乎完美的相关性,但在考虑子量表得分时可靠性较低。
共情量表(Pommier, 2010)——一个包含24个项目的自我报告量表,针对普通人群,基于共情由善良、正念和共同人性组成的理论。
关系共情量表(Hacker, 2008)——一个包含16个项目的量表,采用4点量表从“不同意”到“强烈同意”。该量表包括四个子量表,分别测量受访者的共情对他人的态度、对自己、他人是否彼此共情,以及他人对自己共情的态度。
关怀照护评估工具(Burnell & Agan, 2013)——一个包含28个项目的量表,旨在测量医院环境中护理人员展示的共情水平。与其它量表不同,此量表由患者完成,以评价其护理人员的共情表现。
Schwartz关怀照护量表(Lown, Muncer, & Chadwick, 2015)——一个包含12个项目的量表,旨在测量患者对其住院期间医生的关怀照护成功程度的评分。患者使用10分制从1(完全不成功)到10(非常成功)进行评分。
共情量表
也称为自我共情量表,由Neff(2003)开发,包含26个陈述——13个正面陈述和13个负面陈述,用于衡量在艰难时期对自己典型行为的反应。每个回答都在五点李克特量表上评分(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该量表包含6个子量表,即:自我善意、自我判断、正念、共同人性、孤立感和过度认同。
共情量表由13个正面陈述和13个负面陈述组成,这些陈述测量了在艰难时期对自己典型行为的反应。每个陈述在五点李克特量表上评分(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该量表包含六个子量表:自我善意、自我判断、正念、共同人性、孤立感和过度认同。
共情量表由Neft(2003)开发,包含26条陈述,旨在衡量在困难时期对自己的典型行为。每个陈述在五点李克特量表上评分(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该量表包含6个子量表:自我善意、自我判断、正念、共同人性、孤立感和过度认同。
共情量表由13个正面陈述和13个负面陈述组成,用于衡量在艰难时期对自己典型行为的反应。每个陈述在五点李克特量表上评分(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该量表包含6个子量表:自我善意、自我判断、正念、共同人性、孤立感和过度认同。
共情量表的编制包括以下陈述:
- “我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持批判和评判的态度。”
- “当遇到困难时,我会善待自己。”
- “当我感到情感上的痛苦时,我会尽力安慰自己。”
每个正面和负面陈述都与共情的四个要素相关:理解苦难的普遍性、情感共鸣、容忍痛苦情绪的能力,以及采取行动或行动以减轻苦难的愿望(Strauss et al., 2016)。
最近,Raes等人(2011)开发了一个12项的简短自我共情量表,其中选取了自共情量表中的六个正面和负面陈述,并采用相同的评分方式。
对他人的共情量表
共情是西方心理学中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领域。此外,心理学家越来越对佛教关于正念和共情的概念感兴趣。因此,需要开发一个量表来衡量这一概念,以便对共情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研究。
已开发出多个量表和测量方法专门用于衡量对他人的共情。这里我们将探讨Pommier的共情量表和Martins等人(2013)的共情量表。
基于自我共情量表,共情量表(Pommier, 2010)旨在将自我共情的理论结构转化为对他人的共情。共情量表的根本目标是测量由Neff(2003)定义的共情:“被他人的痛苦所触动,敞开心扉感受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回避或脱离,从而让对他人的善意和希望减轻其痛苦的愿望浮现出来”。
当完成共情量表时,参与者需阅读24个陈述,并在五点应答量表上进行评分,范围从1(几乎从未)到5(几乎总是)。
陈述通常以口语而非语法正确的语言编写,以反映人们自然交谈的方式,避免使用令人困惑或过于复杂的语言。
量表包括以下陈述:
- “有时当别人谈论他们的麻烦时,我觉得我不在乎。”
- “我不太在意别人的忧虑。”
- “当别人感到悲伤时,我会尽力去安慰他们。”
- “我的心为不开心的人跳动。”
共情量表的开发使得共情可以接受科学分析,并可用于评估:
- 佛教实践(如冥想)的效果。
- 共情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
- 共情对负面心理状态的积极影响。
- 心理咨询和治疗领域。
- 医疗行业和教育环境中的关怀照护要求,这些领域将受益于一种关怀的立场。
Martins等人(2013)的共情量表是一个10项的自我报告量表,旨在测量共情的五个维度,即:慷慨、热情好客、客观性、敏感性和宽容,涵盖所有社交网络和关系,采用7点应答量表。
该量表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可以增强训练的共情测量,作者认为其他量表不适合以可针对教育的方式衡量共情。
该量表侧重于共情的实际方面,如向他人提供财务帮助、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为他人服务,以及在对家人和朋友或家庭的风险或牺牲的情况下为他人做事。因此,该量表不包括与识别痛苦、情感共鸣和容忍不舒服的感觉相关的项目(Strauss et al., 2016)。
给自己许可做一个普通人
对自己友善意味着允许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
人类会犯错,身体并不完美,也不总能高效工作,也不是完美的朋友、父母或配偶。
我们必须放下这种僵硬、完美主义的盔甲,当我们生活艰难时,对自己展现善意和共情。
当你的思维开始批判时,反思并练习对自己说这些话。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奇怪,但当你开始给自己许可做一个普通人时,你会感到解脱,并提高自己的自我共情。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