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犯:定义、原因及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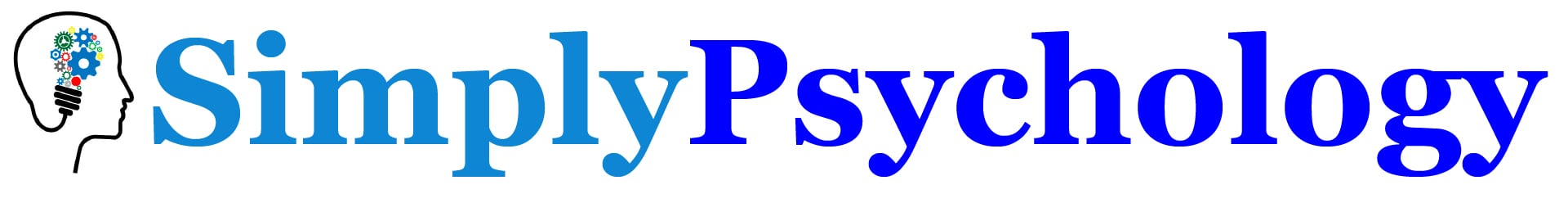
再犯:定义、原因及案例

定义
再犯指的是罪犯重新犯罪的行为。再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然而,所有现有的定义都具有三个共同特征(Zgoba 和 Salerno, 2017)。
首先,再犯需要有一个起始事件,例如从刑事羁押中释放或完成康复计划。
其次,在此事件之后需要有一些失败,例如再次被捕或因暴力犯罪再次被捕。
第三,需要有一个再犯窗口期或随访期,在此期间罪犯的进一步行为可以被视为再犯。
在每种情况下,再犯最终都指一个人在受到制裁或因先前犯罪接受干预后重新犯罪的行为(Zgoba 和 Salerno, 2017)。
政府通过在罪犯释放后三年内导致再次逮捕、再次定罪或返回监狱(无论是否有新的判决)的犯罪行为比例来衡量再犯率。
再犯率
美国
司法统计局对1983年和1994年释放的囚犯进行了再犯研究(Beck & Shipley, 1989; Langan & Levin, 2002)。
根据这些研究,1983年释放的囚犯中有近63%在三年内再次被捕,47%被新定罪,41%返回监狱。
这些再犯率在第一年最高,四分之一的获释囚犯在释放后的前六个月内再次被捕,五分之二在释放后的第一年内再次被捕。
这些监狱中有26%在释放后至少被指控20项罪行,5%被指控45项或更多罪行。
到1994年,再犯率上升,68%的获释囚犯在三年内再次被捕,47%被新定罪,25%因新罪名再次入狱。
在释放后三年内,这一数字上升到52%(Langan & Levin, 2002)。
英国
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期间,成年罪犯在释放后一年内的再犯率(再犯)为45.8%。
服刑时间少于12个月的成年人再犯率为59.8%,而服刑时间12个月或以上的成年人再犯率为33.9%。
同期青少年的再犯率为67.1%。在更长的时间内,再犯率约为57%。
这是欧洲最高的再犯率。
原因
再犯有许多潜在的原因(Zgoba 和 Salerno, 2017):
- 监禁期间的社会互动,
- 缺乏就业和经济机会,
- 抑郁,
- 缺乏重新融入社会,
- 释放后生活方式和社会圈子未改变,
- 监禁期间未解决导致犯罪的根本问题。
Otu(2015)在研究尼日利亚监狱系统时指出,再犯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
最明显的是社会对监禁的反应。随着平民对已释放和未释放的囚犯采取歧视态度,被定罪的人由于标签和污名化难以重新融入社会。
为什么监狱不起作用?
- 监狱没有解决导致囚犯最初犯罪的心理问题,例如道德发展不良和归因偏差或心理健康问题。
- 人们被释放到与他们原来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社会剥夺和失业。
- 被监禁的污名使得重新融入社会变得困难,例如找工作。此外,他们与相同的人交往(差异关联理论)。
- 对一些人来说,监狱比他们离开的生活更好;他们有同伴、食物和温暖的住所。
其他学者,如Giddens(2006)和Obioha(1995),认为将犯下不同罪行的囚犯以及具有不同背景、行为和个性特征的囚犯关在一起,会导致监狱内部形成犯罪亚文化。
在这种观点中,监狱成为犯罪的“学校”和犯罪社会化滋生地。
与此同时,Tenibiaje(2013)对再犯原因采取了更广泛的方法,声称预测再犯的因素分为情境、个人、人际、家庭、结构、文化和经济类别。
Gendreau, Little 和 Goggin(1996)在其元分析中指出,静态风险因素是导致再犯的原因。这些风险因素包括性别、首次定罪年龄、父母是否有犯罪记录、当前年龄和所犯罪行类型。
此外,Gendreau, Little 和 Goggin 认为所谓的动态风险因素是再犯的最强预测因子。这些动态因素包括“犯罪需求”,涉及犯罪同伙、犯罪史或反社会行为史、社会成就和家庭结构。
Brown(2002)也得出结论,犯罪同伙、反社会态度以及当前就业和教育问题都是再犯的强烈预测因子。
其他关于再犯原因的研究维持,参与非犯罪活动(如就业和教育)的低参与度是犯罪再犯的风险因素(Skeem & Peterson 等,2010)。
一些研究人员进行了再犯研究,以确定某些治疗计划是否有效减少再犯。
根据这些研究,同伴群体影响是再犯的一个有力预测因子,尽管在青少年罪犯中比成年罪犯中更为普遍。
Beesley 和 McGuire(2009)认为,群体影响通过模仿和示范促进直接行为学习而起作用。此外,一些犯罪,尤其是青少年和年轻人中的犯罪,可以在群体环境中实施。
与同伴群体相关的分散责任以及同伴压力可能鼓励更大的实验行为,而这些行为单独进行时可能不会发生。
这些同伴效应同样适用于家庭和朋友——多项研究表明,与从事犯罪行为的朋友和家人相处时间较长是犯罪和再犯的强烈风险因素(Murray 和 Farrington, 2010)。
另一个再犯的风险因素是物质滥用。使用毒品的青少年比不使用者更容易参与暴力行为(Dawkins, 1997),药物滥用还与家庭和婚姻问题高度相关。
缺乏家庭关怀时,青少年和年轻人会转向毒品作为应对歧视和污名化的手段。
然而,这给监狱后的康复、融入和适应带来了更大的困难(Leschied, Chiodo, Nowicki, & Rodger, 2008)。
案例
Pew 关于再犯率的调查
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再犯率的调查。
2011年的Pew-ASCA调查发现,1999年获释的罪犯中有45.4%在三年内再次被监禁,而五年后这一数字仅减少了2.1%。
再犯率通常因对再犯者施加重罚的存在与否而有所不同——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三次打击”量刑法(Greenwood, Rydell, Abrahamse, Caulkins, Chiesa, Model, & Klein; 1994)。
尽管如此,美国大州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再犯率已显著下降,导致全国整体再犯率呈下降趋势。
然而,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数据从这些调查中排除时,总体国家再犯率似乎保持稳定(Zgoba & Salerno, 2017)。
元分析
Smith等人(2002年)对100多项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研究了再犯、刑期长度以及监禁与非监禁判决之间的关系。
他们发现,监禁后的再犯率并不低于非监禁判决,且较长的刑期并未降低再犯的风险。
欧洲再犯率最低的是挪威。其监狱系统非常不同,更加开放,更注重康复和技能获取,而非英国的系统。
尼日利亚监狱系统的再犯问题
Otu(2015年)分析了尼日利亚监狱系统中的再犯原因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减少再犯的可能方法。
Otu指出,尼日利亚监狱系统缺乏采购和建立先进的矫正项目(如职业培训和正规教育系统)的资源。
实际上,现有的设施往往条件较差或使用的技术已经过时,不适合现代劳动力市场。
因此,很少有囚犯在释放时接受正式的康复,常常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和可接受的学术资格,以在外界找到工作。
这导致了不稳定的就业和低收入,教育和技能培训项目的质量低下,高犯罪率的社区环境,以及主流社会对他们的社会污名化。
再犯给尼日利亚的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一个直接的成本是尼日利亚纳税人的负担,尤其是在政策增加监狱人口时,导致更高的预算需求(Chukwumerije, 2012年)。
Otu(2015年),根据McKean和Ransford(2004年)的建议,提出了可以成功减少再犯的三个主要项目要素:物质滥用或精神疾病的治疗、教育和有意义的就业。
这些措施消除了就业和融入社会的障碍,使囚犯具备在外找工作所需的技能,并通过提供收入和支持重新融入社会来提高稳定性和自信心。
预防
为了减少再犯(即再犯罪),惩罚需要既适合个人也适合犯罪行为,还需要更多研究来减少监禁带来的负面心理影响。
目标应该是让罪犯离开监狱时完全改过自新,准备好成为有生产力和守法的公民。
监禁的替代方案 ——鉴于我们知道监禁无效,我们需要寻找替代方案。一些替代方案包括缓刑和恢复性司法。
然而,由于经济限制和公众意见,政府不愿意投资于囚犯。但这是短视的做法。为了减少犯罪和再犯率,需要进行投资(经济影响)。
从行为主义视角来看,监禁可能会起作用,但它没有起作用,因为它没有遵循操作条件反射的原则。
为了学习的发生,惩罚必须是可能的(即,它必须总是或几乎总是跟随行为)、及时的(即,必须紧随行为之后)且非常令人不快。
然而,许多罪犯并没有被抓到(或不是每次犯罪都会被抓到),而且惩罚并不及时,因为从犯罪到被捕、定罪和送入监狱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监禁对大多数囚犯来说是不愉快的,但犯罪还有其他后果,例如经济利益或其他形式的满足感。
再犯的重要性
再犯是考虑刑事司法几个核心议题的重要特征,如剥夺自由、特殊威慑和康复。
剥夺自由是指旨在通过将犯罪分子从社区中移除来阻止其犯罪的行为对社区犯罪率的影响。
特殊威慑是指制裁(如逮捕)是否在实施或完成后能阻止人们再次犯罪。
最后,康复是指通过解决犯罪者的需要和缺陷,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犯罪。
政府机构还利用再犯率来评估监狱的表现,并研究私营和公立监狱管理的有效性差异。
简而言之,如果罪犯在释放后停止犯罪,监狱就被认为更成功。最终,犯罪终止发生在个体成功维持永久无犯罪状态时。
批评
衡量治疗和项目效果的再犯率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这些不一致使得评估矫正技术和治疗变得困难。有几种方法论上的原因(Zgoba 和 Salerno, 2017年)。
再犯率变化的第一个原因是研究人员如何定义再犯。再犯可以定义为任何新的犯罪或指控,也可以定义为任何新的特定犯罪。
例如,因性犯罪被判刑并关押的人,其再犯率可以通过他们是否再次被定罪为另一项性侵犯,或者是否因任何犯罪(如逃税)被定罪来衡量。
Rice、Quinsey 和 Harris(1991年)发现,在六年的跟踪期内,58%的样本因任何新的犯罪被捕,而因新的性犯罪被捕的比例为31%。
增加再犯定义复杂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调查人员是否将技术违规或在机构或监狱内的违规视为再犯。
例如,将违反假释规定定义为再犯会扩大其定义,可能导致更高的再犯率(Zgoba, Sager, & Witt, 2003年)。
再犯率测量的另一个变化涉及用于测量再犯的数据的有效性——报告实际再犯率的准确性。
再犯数据可以包括再逮捕、再定罪和再监禁的测量,每种测量的有效性水平可能不同。
例如,基于再逮捕数据计算的再犯率可能准确度较低,因为许多案件不会进入定罪阶段。
同时,基于再定罪或再监禁的再犯率可能反映更高的准确性。一般来说,使用再逮捕数据测量再犯率的研究比使用再监禁数据的研究再犯率更高。
此外,具体的法律程序,如认罪协商,可能导致不一致,从而不成比例地导致定罪(Zgoba 和 Salerno, 2017年)。
另一个影响再犯率的因素是犯罪分子群体内的聚合。许多研究将犯罪分子视为同质群体,而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型的犯罪分子之间的再犯统计差异。
然而,这只有在犯罪分子确实是同质群体时才有效——有证据表明,相反,犯罪分子在其犯罪模式上极其异质。
据报道,强奸犯的再犯率最高,其次是儿童性侵犯和乱伦犯(Deming, 2008年;Freund, Watson, & Dickey, 1991年)。
将所有性犯罪者视为同质群体时,该群体的再犯率实际上是一个平均过程,其中再犯率由样本中不同类型犯罪者的代表性加权(Zgoba & Salerno, 2017年)。
第四个影响再犯率方法的因素是再犯的后续时间窗口有多宽。后续时间越长,犯罪分子再犯罪的机会窗口就越宽,因此再犯率越高。
最近的再犯研究集中在更长时间间隔上,以允许足够的时间来有效代表再犯罪模式(Zgoba & Salerno, 2017年)。
第五个挑战是许多再犯研究缺乏对照组。出于伦理原因,犯罪分子很少被分为治疗组和非治疗组。这使得很难测量治疗对再犯率的影响。
再犯研究中的最后一个方法论难题是认为犯罪者必然会再次犯罪的观念。这种信念通常伴随着高再犯率。
因为许多人认为犯罪者是精神错乱且无法治疗的,所以犯罪者可能被驱逐到社会边缘,从而激发进一步的犯罪行为(Zgoba & Salerno, 2017年)。
参考文献
Beck, A. J., & Shipley, B. E. (1989). Recidivism of prisoners released in 1983.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eesley, F., & McGuire, J. (2009). Gender-role identity and hypermasculinity in violent offending. Psychology, Crime & Law, 15(2-3), 251-268.
Chukwumerije, U. (2012). Explanatory memorandum on amendment of prison act. (On-line: http://www.Senatorchukwumerije/id63html
Dawkins, M. P. (1997). Drug use and violent crime among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32(126), 395.
Deming, A. (2008). Sex offender civil commitment programs: Current practices,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dent demographics. The Journal of Psychiatry & Law, 36(3), 439-461.
Freund, K., Watson, R., & Dickey, R. (1991). Sex offenses against female children perpetrated by men who are not pedophil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8(3), 409-423.
Gendreau, P. Little, T. & Goggin, C. (1996). A meta-analytic of the predictors of adult offender recidivism: what works? Criminology, Vol. 34: 575–608.
Giddens, A., & Sutton, P. W. (2006). Sociology (Vol. 19932). Polity Press.
Greenwood, P. W., Rydell, C. P., Abrahamse, A. F., Caulkins, J. P., Chiesa, J., Model, K. E., & Klein, S. P. (1994).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Estimated benefits and costs of California’s new mandatory-sentencing law. Santa Monica, CA: Rand.
Langan, P. A., & Levin, D. J. (2002). Recidivism of prisoners released in 1994.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Leschied, A., Chiodo, D., Nowicki, E., & Rodger, S. (2008). Childhood predictors of adult criminality: A meta-analysis drawn from the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litera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50(4), 435-467.
McKean, L. & Ransford, C. (2004). Current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recidivism. (On-line: http://www.targetarea.ord/research.doc/
Murray, J., & Farrington, D. P. (2010). Risk factors for conduct disorder and delinquency: key findings from longitudinal studie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5(10), 633-642.
Obioha, E. E. (2011). Challenges and reforms in the Nigerian prisons system.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7(2), 95-109.
Otu, M. S. (2015).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recidivism in the Nigerian prison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Review, 10(1), 136-145.
Peterson, J., Skeem, J. L., Hart, E., Vidal, S., & Keith, F. (2010). Analyzing offense patterns as a function of mental illness to test the criminalization hypothesis. Psychiatric services, 61(12), 1217-1222.
Rice, M. E., Quinsey, V. L., & Harris, G. T. (1991). Sexual recidivism among child molesters released from a maximum security psychiatric institu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9(3), 381.
Tenibiaje, D. J. (2013).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eer group influence as predictors of recidiv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 5 (1): 30– 37.
Zgoba, K. M., Sager, W. R., & Witt, P. H. (2003). Evaluation of New Jersey’s sex offender treatment program at the Adult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Center: preliminary results. The Journal of Psychiatry & Law, 31(2), 133-164.
Zgoba, K. M., & Salerno, L. M. (2017). A three-year recidivism analysis of state correctional releases. Criminal Justice Studies, 30(4), 331-345.
进一步阅读
Latessa, E. J., & Lowenkamp, C. (2005). What works in reducing recidivism. U. St. Thomas LJ, 3, 521.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oven re-offending following release from prison
Transforming Rehabilitation: a summary of evidence on reducing reoffending
引用来源
本文翻译自以下网站:
simplypsychology.org
使用声明
本文仅供教育和参考用途。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和作者。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随时联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