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伤中恢复的科学
是什么使我们能够从创伤性经历中走出来?心理学家发现,这并不总是关于迅速恢复——有时候我们必须感受到整个世界分崩离析。
- 作者:Sharon Begley
- 2019年3月7日
- 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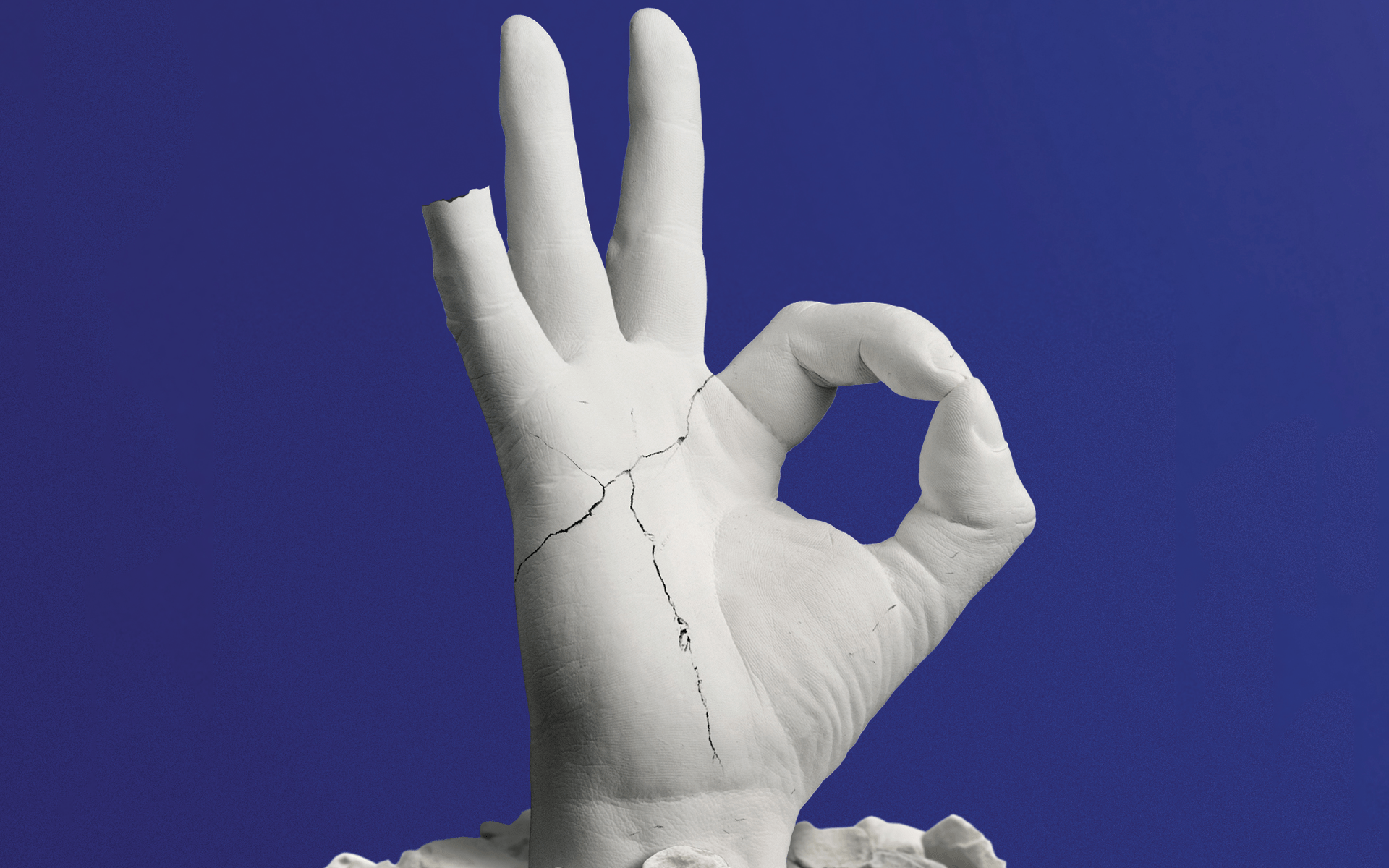
Edmon de Haro
这位越战老兵在年轻时参军,经历了两次战斗巡逻,并在多次激战中幸存下来。“直到今天,”耶鲁医学院的心理学家Jack Tsai说,“某些气味仍然会触发他的战争记忆,使他想起越南:茂密的植被、刺鼻的燃烧气味,甚至是汗水——就像那些在闷热丛林中为生命而战的人们脸上流淌的汗水——这一切都会让他回忆起一切。”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而,在Tsai治疗他(成功)的过程中,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老兵仍然将他的越南经历描述为恐怖的,但他表示这些痛苦的记忆提醒他自己的身份。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研究心理学家对创伤的新理解:当人们最缺乏复原力——即他们被彻底打乱,无法快速或完全恢复,并且在数月甚至数年内情绪上饱受折磨——他们最终可能会从创伤中变得更坚强、更珍惜生活、更同情他人,并且拥有不同(可能是更为开明)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通过任何想象力都无法称这位老兵具有复原力,因为按照研究心理学家所用的术语,复原力是指在经历巨大逆境后仍能继续生活,心理和情感上基本保持不变的能力。相反,环境触发因素将他的思绪带回了地雷、伏击和朋友丧生的恐怖场景。同时,老兵的军事经历(以及他对PTSD的克服)使他感到自己可以完成任何事情。“没有什么能困扰他,因为与越南相比,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Tsai说。
对许多人来说,创伤后的成长带来了更亲密的关系——家庭和其他亲人更加被珍惜——并且与同样遭受痛苦的人建立了更强的联系。
这种效应,称为创伤后成长,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心理学家Lawrence Calhoun和Richard Tedeschi于1996年命名的。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都涉及积极的心理变化:更强的个人力量感(“如果我能在那件事中幸存,我就能应对任何事情”),更深的精神意识,对生活的更大感激,以及认识到以前未见的人生路径和可能性。对许多人来说,创伤后的成长带来了更亲密的关系——家庭和其他亲人更加被珍惜——并且与同样遭受痛苦的人建立了更强的联系。
比以往更强大
伟大的苦难带来伟大智慧的概念既古老又熟悉。我的一位肿瘤科朋友谈到癌症患者说,癌症是他们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因为它切除了生活中通常的琐事,让他们重视真正重要的东西。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幕僚长Hamilton Jordan(1944–2008)说他与癌症的斗争让他看到“简单的快乐无处不在,而且是无穷无尽的。”
在我童年的朋友Joyce在20岁时因车祸失去右腿后,她几个月的康复和康复训练让她有无数空闲时间思考。“以前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比如受欢迎,现在不再重要了”,我记得她说过。“我关心的是有所作为【她成了一名小学教师】,我觉得我更有同理心。我觉得当有人在受苦时,我能深刻理解她的感受。以前,这只是‘哦,真可怜’。”
然而,创伤后的成长并不意味着创伤是可取的,更不应在他人遭遇不幸时轻描淡写。正如畅销书作家拉比哈罗德·库什纳在他儿子14岁去世后获得的精神成长所说:“如果我能把他带回来,我会立刻放弃所有这些收获。”
很少有人的生活没有痛苦、危机和创伤,从极端或罕见的事件,如成为战争难民或被劫持为人质,到常见的事件,如丧亲、事故、火灾、战斗或自己或亲人的严重或慢性疾病。多年来,正念一直认为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最佳方法——以及对创伤的反应远低于心理障碍——是复原力,即在面对逆境时恢复并从中学习、改变和获得力量的能力。现在,随着正念将创伤后成长作为研究的重点,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理解,即创伤、复原力、PTSD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复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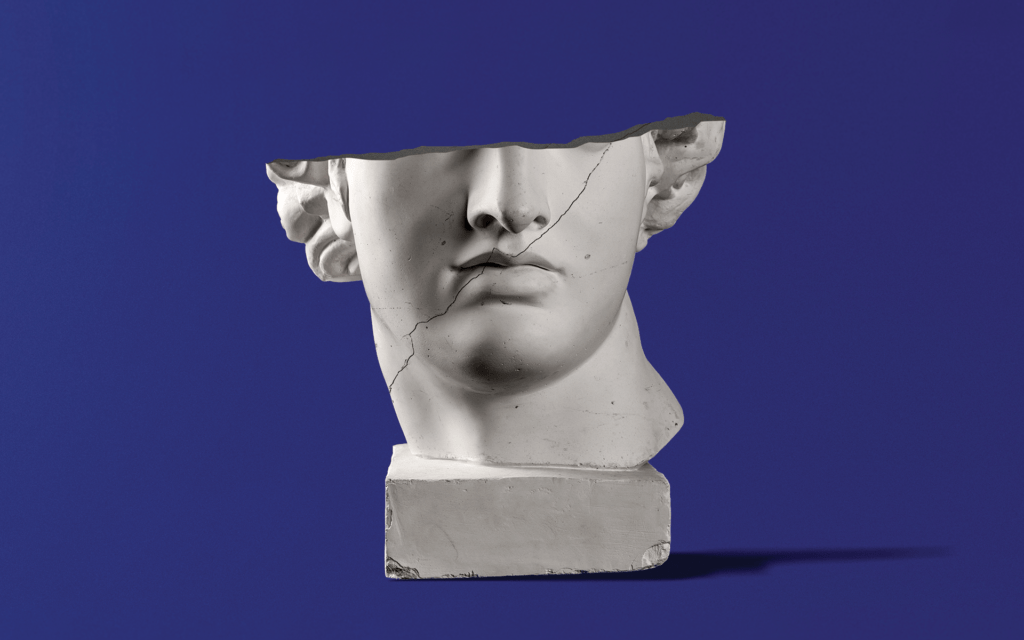
创伤后成长与复原力
尽管心理学上的复原力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科学家仍在努力理解其起源。一些研究表明,它是在童年时期由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建立的强有力关系以及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信念所培养的。但相反的信念,即“上帝掌控一切,一切都有其原因”,也可能有助于复原力,北卡罗来纳大学的Calhoun说。2016年对来自南苏丹、乌干达、波斯尼亚和布隆迪等九个国家经历过暴行和战争的人们的回顾发现,复原力因文化而异。强烈的情感连接在某些社会中促进了复原力,但在其他社会中并非如此,而自我决定感实际上在某些人中适得其反:如果你相信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看到家人在萨拉热窝被狙击手射杀,你不仅会感到悲痛,还会感到沉重的内疚。
在缺乏复原力的情况下,创伤后成长——对创伤的一种非常不同的反应——可能会出现。 “创伤后成长意味着你已经被打破——但你重新组装了自己”以更强大的、更有意义的方式,Tsai说。这一观点可能令那些认为复原力是在面对逆境时学习、改变和获得力量能力的人感到惊讶。然而,在研究心理学家中,复原力是指相对轻松地回到创伤前的状态,而不一定是前进到一个更强大的地方。根据这种理解,如果没有破裂,就没有重新组装,因此具有强大应对能力的人受到创伤的挑战较小,因此不太可能经历创伤后成长。
在缺乏复原力的情况下,创伤后成长——对创伤的一种非常不同的反应——可能会出现。
为了发生创伤后成长,破裂不必像那位越战老兵那样极端到构成PTSD。Tsai和他的同事发现,在他们研究的1,057名美国退伍军人中,平均每人一生中有5.7次创伤(包括丧亲、自然灾害、疾病和事故,以及军事创伤)。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患有PTSD,但59%的退伍军人经历了创伤后成长。而且,最强的预测因子是某人在经历额外创伤后避免PTSD是否曾经历过创伤后成长,Tsai和他的同事在《情感障碍杂志》上报告。这是第一个研究之前创伤后成长是否可以在再次遭遇创伤时保护人们免受PTSD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创伤后成长实际上可能增强复原力。
创伤后成长——与复原力不同——不是回到基线。它是重新组装你“对世界/宇宙和你在其中的位置的一般信念体系”的产物,Calhoun说:你质疑世界的善良、可预测性和可控性,你的自我认知,你期望的生活轨迹。从先前信念的碎片中,你创建全新的世界观,并可能成为一个比以前更强大的人。
什么是创伤?
在精神病学界,什么构成“创伤”是有争议的。有些人根据事件的性质定义创伤:例如,精神病学的诊断手册指出,创伤性体验必须超出人类通常遇到的范围。其他人则根据人们对经历的反应来定义创伤:强烈的恐惧、无助、恐怖或痛苦是创伤的症状。
循环定义——“创伤是让你感到创伤的事情”显然不理想。而“超出正常经验范围”也不是可靠的衡量标准:悲剧性的是,许多曾经超出这个范围的经历如今已不再是,例如自然灾害、大规模枪击事件或战争的恐怖。
学者们正试图做得更好。新兴的定义认为,创伤挑战了一个人的“假设世界”:她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世界运作方式以及她的生活如何展开的信念。根据这种理解,创伤不必威胁生命或健康,也不必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它必须让你质疑你最基本的假设,例如世界是公平的,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人类的不人道行为是有极限的,事情总会好起来的,或者老者先于年轻人离世。根据这种定义,我们中很少有人能在这世上度过而不经历创伤。